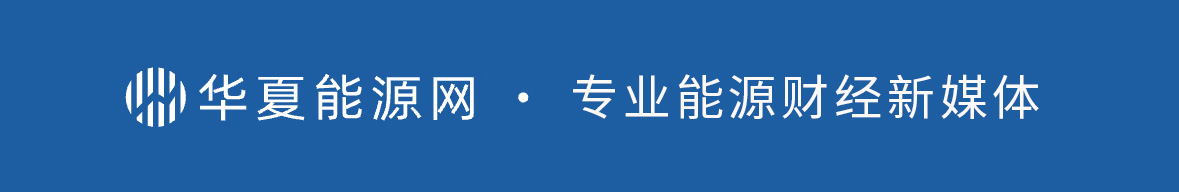投稿与合作
欢迎来到华夏能源网,如有新闻报道、品牌传播、稿件发布需求,请按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一、免费发布:我们欢迎能源、财经及相关领域有较强新闻价值、较高思想水准的优质稿件,请附上联系方式投稿至tougao@mail.hxny.com,我们将择优、免费刊发。如48小时内没有回复,请自行处理您的稿件。 二、定制服务:如果您有更多的产品宣传、公关传播需求,我们很乐意为您提供专业的定制化服务,欢迎垂询QQ/微信:805922102,邮件:hezuo@mail.hxny.com。

作者 / 蔡译萱
来源 / 南方能源观察
年中,全球疫情未能如期被“扑灭”,而持续已久的中美贸易摩擦也并未停下脚步。世界经济发展承压,提升产业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成为焦点议题。
20世纪80年代末,产业在全球范围内根据比较优势分布,与产品相关的完整产业链相应地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形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从不同产业的全球分工到产业内的全球分工,再发展到企业内的全球分工,形成了生产、流通、服务链条更加紧密的全球价值链。
在新冠疫情冲击之下,这种紧密的联系遭遇挑战,全球化显现“慢球”(slobalization)特征。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要发挥好宏观政策协调机制作用,更加注重产业链协调复工复产,积极应对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不稳定风险挑战。要更加注重消除供需两端“温差”,把长期和短期结合起来,做好扩大内需这篇大文章。
能源企业在“慢球”中际遇如何?我国能源产业链中哪些环节仍被“卡脖子”?哪些环节需要加强自主研发能力?又有哪些环节应该坚持全球化配置?
以电网、核电和燃气轮机三大技术资产密集型行业为例,安全、效率和经济性仍是决定自主投入还是开放引进的三个关键因素。
“国内有那么大的规模化需求,就不可能长期靠外资了。”一位长期从事天然气业务的人士判断。在中国,燃气轮机似乎正在成为一盘“大生意”。
根据中国《天然气发展“十三五”规划》,截至2015年底,中国天然气发电装机量为5700万千瓦;到2020年,天然气发电装机量将达到1.1亿千瓦以上,在发电总装机量中的比例将超过5%。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9年底,上海电气已签订12台燃机长协服务订单,新增燃机设备订单人民币65.5亿元,同比增长630.7%;报告期末,在手燃机设备订单人民币105亿元,比上年年末增长41.9%。
截至2019年,东方电气和三菱的合资公司已取得超过70台大型燃气轮机订单,实现燃气轮机年产能15套。
自1939年世界第一台发电用重型燃气轮机在瑞士诞生以来,世界燃气轮机市场上最初的老大是瑞士BBC,后来美国GE、德国西门子崛起,而后日本三菱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进,企业不断兼并重组,GE、西门子、三菱各自具备完整的技术体系和产品系列,逐渐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
目前在国际市场上,西门子、GE、三菱重工性能优良的燃机完全可以满足全球市场需求,中国为何还要自己研发制造?
燃机本身商业价值巨大,一套商用F级机组的价格大约是5亿元人民币,能拉动产业链数以亿计的价值,仅热部件就达1亿元人民币。而每年单台机组需向外商厂家支付两三千万元,国产燃机的费用仅为其1/3甚至1/4。
据了解,当前国内主机厂商在装配制造技术的国产化上仅取得了阶段性成功,如能突破设计、试验、维修维护等环节,才可视为实现了自主化。而商业上的成功,政策支持当然有帮助,最终还是得由市场决定。
中国燃机能不能“弯道超车”?以当前国内主机厂商对核心技术和供应链的把控能力看,要想实现并不容易。尽管如此,国内许多制造商仍然没有放弃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燃机的目标。
从苏联技术到打捆招标
国内重型燃气轮机产业建立于1950年代,与发达国家相比起步并不晚。但60多年来行业的发展基本呈马鞍型,与发达国家差距不小。
上世纪50到70年代,在消化吸收前苏联技术的基础上,中国自主设计、试验和制造开发出200—25000kW多种型号的燃气轮机。清华大学、哈尔滨汽轮机厂(哈汽)、上海汽轮机厂(上汽)、南京汽轮机厂(南汽)、中国北车集团长春机车厂(长春机车)、青岛汽轮机厂(青汽)、杭州汽轮机厂(杭汽)等都曾投入到燃气轮机早期的研制,全行业技术水平进步很快,但当时主要采取测绘仿造与自主研发相结合的方式,处于跟踪设计阶段。
1976年,以南汽为首的全国近百个单位通力合作,主要测仿美国GE公司的一款燃气轮机,研制成功了两万千瓦燃气轮机发电机组成套设备,可谓是行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中国科学院院士蔡睿贤曾在著作中指出,当时也有些企业试图完全自主研发燃气轮机,有成功的案例,但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都停滞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维斗曾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感慨,那时候如果下功夫加紧研究也能上去,可以说若干历史阶段都有机会,但都没有把握住,就像狗熊掰棒子,错过了很多机会。如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诸多燃气轮机中有连续做下去的,说不定就能做出商用产品。
但历史没有假设。
1980年代到2000年,国内燃气轮机产业以仿制与合作生产为主,不再自行研究、设计和试验燃气轮机产品。那时以南汽为主测绘、仿制了GE公司MS5001(23MW)燃气轮机,并与GE合作生产了PG6581(6B/36MW)燃气轮机。
但受困于全国油气供应严重短缺,国家不允许使用燃油、燃气发电,重型燃机失去市场需求,全行业进入低潮。除保留南汽外,其他制造企业全部下马,人员和技术流失。加上大学燃机专业改行,人才培养和国家研发投入基本停止,国内燃机产业与国际水平差距迅速拉大。
而随着西气东输项目上马,国内开始投建燃气轮机电厂,国际巨头也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市场。
2001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燃气轮机产业发展和技术引进工作实施意见》,决定以市场换取技术的方式,引进、消化、吸收燃气轮机制造技术。
在2001—2007年的6年间,中国以“打捆招标、市场换技术”的方式,引进了GE、三菱重工、西门子公司的F/E级重型燃气轮机50余套共2000万千瓦,由哈汽—GE、东汽—三菱重工、上汽—西门子、南汽—GE等4个联合体实行国产化制造。
当时主持这一工作的时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曾在多个公开场合指出,燃气轮机打捆招标的核心是:集中企业采购机组,吸引通过招标选择设备供应商,采购的同时,要求对方转让技术。
在引进过程中,西气东输项目和进口液化天然气(LNG),保证了燃气轮机的燃料供应,也因此带动了国内的装备制造业。但外方坚持不转让燃气轮机设计、热端部件制造等核心技术,国内燃气轮机厂商只能制造非核心部件。
以上海电气为例,2001年从德国西门子公司引进技术,而后又与西门子分道扬镳;2014年,上海电气收购意大利安塞尔多公司40%的股份,成立了合资公司,希望借此研发H级重型燃机技术和市场开拓。
业界普遍认为,虽然在2011年上海电气几乎实现了重型燃机100%的国产化,但未掌握核心技术,仅成为外资企业的组装工厂和销售代表。
与安塞尔多的合作让上海电气能继续使用西门子的燃机技术。引进机组后,上海电气在西门子燃机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新机组在中国市场的销量甚至超过西门子。之后又引进了热部件制造技术,也取得很大进步。
值得一提的是,成立合资公司后,上海电气发展了自己的销售力量,吸纳了包括早期西门子机组的售后服务人员,这种全球化的技术引进和合作方式为国内厂家继续核心技术研发做了技术和服务储备。
从东方电气的情况看,自2002年与三菱重工开展合作,2008年就实现了所有部件国产化制造,目前F4系列的机组全部是国内供货,所有机组的维护也是由国内完成。此外,东方电气也在进行自主技术研发,2019年其研发的国内F级50兆瓦的重型燃机整机试验成功。
引进结合自主研发,从零起步,从最初所有的东西都要送到国外去修,到现在大修的零部件能在国内修,进步很快。有业内人士这样总结,通过与外商公司的合作,中方学习到了先进的制造理念、生产方式,得到了整机的制造技术,也掌握了工艺流程,对中国技术提升有明显促进。
除了与外商的合作,中国也在开展军品往民品转化。一直以来,燃气轮机技术的军民融合是世界性的,英国、美国的许多公司都是军民联产并已形成产业链和样板模式。因此,中国燃机的军民融合也试图从航空发动机派生,通过自主设计和服务实际,逐渐缩小燃气轮机技术与国际的差距。
2010年以前,西气东输、川气输送等大型工程中天然气输送增压机组均是进口设备,因此有研究军品的专家分析了GT28燃气轮机的功率档次,发现其非常适合作天然气压缩机的动力源,提出了对其工业、船用衍生应用与发展研究策略的分析,希望在此基础上全面推进GT28燃气轮机的工业、船用衍生应用与发展。2016年,中船重工第 703所30兆瓦燃气轮机驱动压缩机组,在西气东输三线烟墩压气站完成220小时运行试验,这一燃气轮机正是基于海军052C/D驱逐舰的GT28燃机。
多年来,打捆招标及军民融合让国内燃机人意识到,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自主研究开发燃气轮机核心技术已经成为国内发电设备制造行业的战略需求。
市场换不来核心技术
“知识产权全是人家的,关键部件还要外商提供,出口也受到限制。所以有时我们戏称中国工业产品有心脏病和神经病。”张国宝曾在2016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表示。
重型燃机的自主能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主设计能力,二是对供应商的把控能力。
张国宝说,三菱重工研制的单机70万千瓦重型燃机即将推向市场,并且还可以使用低热值燃气,而我们自主设计的6万千瓦燃机还在图纸上。作为一种复杂的工业产品,燃气轮机涉及多项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必须自主研发。
对于重型燃机的自主设计,包括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技术验证、设计研发、产品生产和应用等。
在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燃机所主任工程师郝洪亮看来,设备企业解决了设计研发、产品制造和应用,但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技术验证确实不是企业能解决的问题。
此外,在与外方合作过程中,外方通过合作协议的约定,限制了重型燃气轮机制造企业的技术改进和品牌创造。合资公司所做出的所有改进一般不允许申请专利,必须提前同外方协商并获得认可的“实质性改进”才能申请专利,且要向外方提供技术细节,在产品上实施要经过外方的许可,但外方却可以直接获得永久的独占许可。这意味着,国内重燃制造企业在对外合作中,很难通过再创新建立自主品牌。
从专利受理区域来看,截止到2016年,美国申请的专利最多,约占专利总数的31%。其次是日本、欧洲、德国、英国等国家或地区。
中国受理的专利仅占专利总数的4%。目前,世界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且能设计制造重型燃气轮机的仅有GE、西门子、三菱等公司。
于是,在“市场换技术”的同时,国内燃机的自主研发工作也同时展开。
2007年科技部启动了973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重大项目“燃气轮机的高性能热—功转换科学技术问题研究”。该项目集结了清华大学、北京航天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大学、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中船重工第703研究所的科研力量,重点研究掌握F 级和IGCC合成气燃气轮机关键科学技术问题,集中力量突破燃气轮机的基础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
清华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系教授蒋洪德曾在著述中指出,在该项目的支持下,共新建、扩改建燃气轮机关键部件压气机、燃烧室和透平冷却实验台3个,开发掌握了激光、压力敏感漆、瞬态液晶、红外、高频动态测量等测量技术,并获得大批基础实验数据,建立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型燃气轮机基础数据库。在该项目中获得的成果已经用于F级重型燃气轮机核心技术、消化吸收和自主研究开发。
在这之后,工信部于2015年启动“两机专项”,开启新一轮“攻坚战”。由国家电投旗下的中国联合重型燃气轮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重燃”)牵头,与哈尔滨电气、上海电气、东方电气等制造企业和高校院所建立协作平台。计划到2023年完成300MW级F级重型燃气轮机产品研制和定型;到2030年,完成400MW级G/H级产品研制。
核心部件制造同样考验自主研发能力。涡轮叶片是燃气轮机工作温度最高的部件,决定了燃气轮机所能承受的温度,但目前重型燃机自主化主要卡在两个方面:高温结构材料、热障涂层技术。从自主制造来看,国内厂商还未掌握F级、E级燃气轮机热端部件制造与维修技术以及控制技术,热端部件也依赖进口。
此外,处于起步阶段的国内燃机厂商对供应商的把控能力也无法与GE、三菱重工、西门子匹敌。欧美的巨头公司早已有意识地在上游布局。
2016年,GE收购了私营企业Metem公司,该公司核心业务是为燃气轮机提供精密冷却孔制造技术,通过拥有这一冷却孔制造技术,能强化GE对燃气轮机产业链的单点控制能力,降低企业成本,作为“布链者”的角色,也相应能控制产业链关键环节。
不过,在制造环节国内厂商正在蓄力。相关业内人士介绍,目前F级燃机的制造技术国产化率有了很大提高,燃气发电机组的运行可靠性也和国外没有区别。重要的是,已经降低了整机造价,以前一套机组要5亿多元人民币,现在降到3亿元人民币。“通过国产化竞争,价格下降了40%,用户成本降低了很多”。
从数量上看,零件的国产化率可以达到80%—90%,但从价值上,还不到70%,也就是说,国产化数量多,但总价值并没有那么高。
作为一国高端制造能力的代表,中国燃气轮机发展的历史上,与高铁核电自主化路径一样: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引进以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有益管理经验。其制造产业特点是国际通行的主制造商加供应商的模式。这也促使作为主制造商的中国燃机厂商,需要在掌握核心技术的基础上,综合国际一流供应商的产品。
而在供应链环节,通过国内公司与供应商成立合资公司的形式,进行一些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学习国际的先进理念和管理水平,而最终还是要增加对供应链的影响力。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燃机产业提升了自主生产能力,降低了用户成本,在短期内缩短了和国际市场的技术差距,促进了整个经济发展也符合国家能源转型的需要,这些都是看得见的进展,但庞大的中国市场和中国制造业的基础能否支撑燃气轮机突破瓶颈,还有待时间的验证。